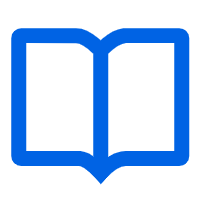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真的吗?
孟姜女的故事是个传说,并非历史真实的。
这个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,把孟姜女与万里长城联系在一起了。相传孟姜女婚姻的悲剧是在长城下得到的补偿。然而,历史的事实是:长城不是埋葬婚姻的坟墓,恰恰相反,长城是维护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坚固堡垒,是保护家庭的“万里长城”。
在奴隶社会中,由于婚姻制度的混乱,出现了妻有再嫁、夫有再娶,以及子女随母嫁入母家等现象,而且妻方在再嫁时,还要带走子女,带走财产,成为争夺财富的起因,所以古代奴隶社会时期,婚姻大事常常成为家庭财产纠纷、血缘关系混乱的祸根,甚至成为家族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。
春秋时期,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管仲。他就认为:“娶妾者,二雌也。不可无别也。别之以地,所以为亲也。妻无限,妾有限。”管仲强调,正妻和妾要有所区别,妻不限其数,而妾则有限。妻如同一家人,可生可养,而妾却是买来的,要卖掉换人。所谓“别之以地,所以为亲”,就是强调妻妾之别要因陋就简地因势利便地表现。
在孔子生活的时代,妻妾制是贵族之家的普遍现象。在《论语·季氏篇》中,孔子谈到季平子,“其弟八人,皆有受业”,可见季氏之弟有妻有妾。在《论语·公冶长篇》中,孔子又谈到:“南容三复白圭。”可见连一个道德之士,都有妻妾。据考古发现。春秋晚期,在临淄的齐国的贵族墓地中,还出现了一批随葬女奴的墓穴,说明奴隶社会里妻妾制的普遍与盛行。
在春秋时期以后的家庭中,还出现了妻妾制的下层、婢妾制。到了战国时期,《周礼》中关于奴婢的规定还十分详细。如《周礼·天官·内宰》提到,“小夫八人,仕四人、徒四人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序官》又规定“府六人……史二人、徒十六人、府史四人、徒四人”。在这里,婢女和男子一样都变成了奴隶。
据司马迁在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中记载,“公仪休相鲁,其妻迎棉。”可见,妻妾制、婢妾制在当时社会中十分普遍。
战国时期,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发展,地主阶级从地主经济中获得阶级利益,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,来维护他们的经济上的优势,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逐步形成。这一发展,引起封建意识形态的兴起与繁荣,以提倡尊孔孟儒学为“君权神授”、三纲五常、父子君臣关系为内容,把奴隶社会的传统观点,例如家庭等级秩序的原则,父权至上的观念等,以“礼教”“三从”等道德规范,来为封建家庭制度和婚姻规定服务。
战国时代的《韩非子》记载着这样一段话“臣有事君,而有不得其死者。其妻不受。其子不葬。臣之罪也,非臣妻与子也。”这是说对君主尽忠而死,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不会接受他的。这是维护封建礼教、君权、父权的一种制度。这种制度又反映到婚姻生活的实际中来。
在封建社会中,妻妾制及婢妾制又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“多妾制”。如“一夫多妻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,是一夫一妻之外的其他妻妾的通称。”(见杨永泉编著《中国封建社会妻妾制度探源》,1988年,兰州大学出版社。)“多妾制”是在儒家“三从四德”,“妻妾有别”,“夫为妻纲”的家庭等级制度下的产物,这是维护封建家庭等级秩序的一种表现,也是封建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,妇女在家庭中是处于从属地位。《礼记·昏义》篇中这样说“夫敬取之以礼,孝终也。妇言不出,妇行不矜,不泄人所不知,故《诗》云‘伐柯伐柯,其则斧,娶妻如之何?必告父母’。”这是说,妇女出嫁后,一切听命于她的丈夫。《易系辞》也说“安土敦乎仁,故曰地不平,尚何用。天地之大德。”这是说天、地、山、川、王、亲,夫、妇、长、幼、尊、卑有守序。这些都是封建道德家庭等级的表现。可见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妻妾制、多妾制是“天经地义”的。
根据孟姜女的故事,孟姜女的丈夫被征召到长城去劳役,由于筑长城而死,她到长城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。这种传说与史实不相符合。历史上修长城的民工的劳役、兵役,是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,不是由官家强迫征召的,不存在强迫百姓去“造长城”的问题,也不存在以夫或妻去长城为役而死。秦始皇虽然实行“发蒙恬”。“戍卒戍边”。但这是法律规定的,不是征召的。秦始皇修长城的劳动力和兵役人员,主要是“发谪徙”。是谪犯人、迁和徒民,还有商人、犯法者、有罪之家本身以及豪强之家因尝罚做成的,都是被“发亦成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记载:“始皇十八年,迁(荆)徒陇西、北地,富、朔,东自函关今河南灵宝东北。,西入于雍,凡三万户”。三万家,“徙谪刑人,充之”这是犯人和刑徒,还有迁商人以及因有罪者、有罪之家都迁到那里去。“徙山东,凡六万户,资之”就是谪戍到东方的六国百姓、还有六国的富户、商人都在那里。这些都是被强迁的,而不是去当什么“造长城”的民夫。